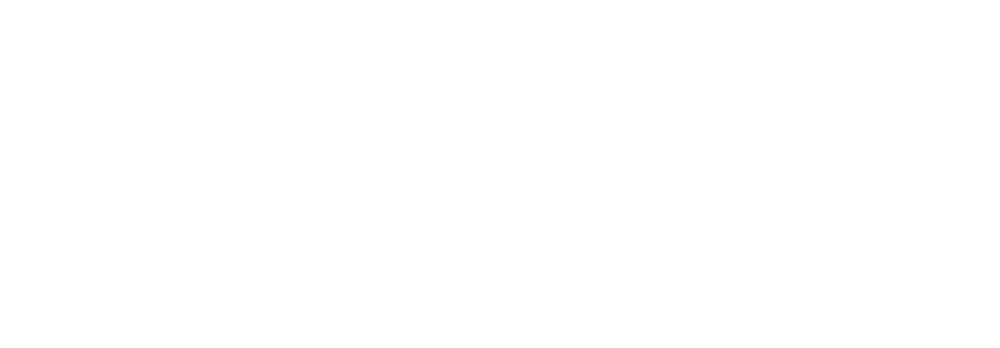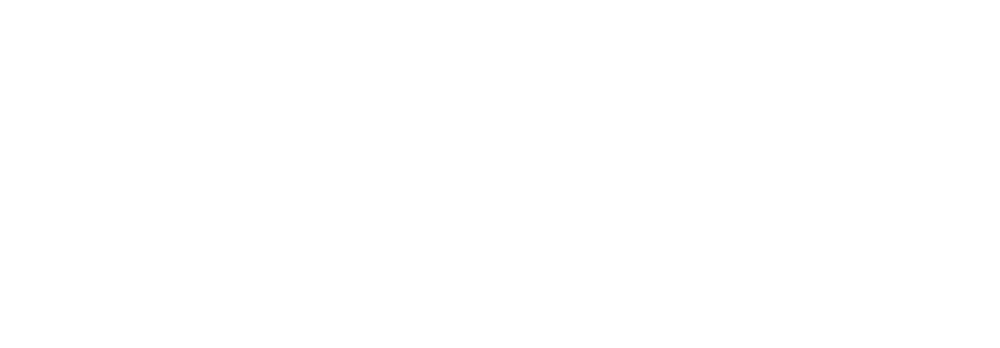一、知識真理(一)對主體真理(多)的必然讓渡
同樣都在2018年11月,緊接《葉瑪》其後,羅蘭.奧澤《在棉花田的孤寂》再次提醒我們將跨國合製與文化交流劃上等號的危機:當徐堰鈴與王安琪大幅度遊走於國家戲劇院生活廣場,透過臺灣的身體,演繹法國導演對法國劇本的詮釋時,與《葉瑪》結構相近的文化權力扞格再次上演。當引入不同國籍、成員、與視角,而成果並沒有在內容顯現出相應的「多」,這樣關於橫的移植之質疑,總一再如不斷歸返的歷史情境被重新突顯出來。其結果展現出的單一性,反映了語言表述與主體經驗的互相衝突。前者拋離後者,成為更高秩序主宰的事實:製作就團隊組成上,由國家兩廳院撮合而成,形成語言層次對「多」價值的強化與重視。此語言意義上的成果,進一步反饋到主辦方,展現出對「多」價值重視的形式。然而回到製作內裏,多的本質並沒有如語言層次展現,它的秩序與價值傳輸大多單向,若有,也僅是為了通往其中一方所設定之目標,而必經之協商與溝通。就此看來,語言意義上的多與經驗意義上的多已經分道揚鑣,成為兩種截然不同、甚至可能對另一方形成威脅的不對等關係。
然而若將劉純良〈多重翻譯,由抽象至表演《葉瑪》〉一文與葉根泉《身體技術作為功夫實踐》一書並讀,可以從相同議題裡梳理出更細緻的層次。身體與文化所牽涉的,並不只是輸出方/輸入方兩種簡單劃分所能完整描繪的。因為當身體作為被辨識、辯證、與討論對象時,便如葉根泉所說:「『主體真理』很可能已經被大寫的『知識真理』所召喚」【1】。換言之,在相關討論裡,只有把「主體真理」也納入辨析的範疇,才可能繼續維持「知識真理」的完整性。後者從客觀、完整的話語結構中,無可避免地讓渡出了缺口,而等待將其填滿的,是不同主體與身體在關照自我過程,所衍生的技術與感受。這個權力位置的位移,標誌了身體與文化討論的典範。客觀「知識真理」原先具有巨大的共構話語範疇;然而面對身體與文化議題,卻只有將真理範疇讓渡給「主體真理」,才得以繼續以語言形式續存下去。劉純良筆下「陌生與歧異」【2】的景觀便是具備相同話語權,並涵蓋不同內容與脈絡的集合。
但是,回歸到個體層次,關照自我與演員修「身」技術從八〇年代小劇場以降,從爆炸性的實驗與突破轉變至今,除了幾度具代表性嘗試,未有自成體系的定論。除了從西方引進的各種身體訓練體系,如葛羅托斯基、麥可.契訶夫、特爾佐布勒斯的酒神訓練外,在地辨明自我身體並建構發展訓練體系的可能性為何?除了「被輸入」之群體與地理空間想像,還有什麼方式可以進一步辨析身體狀態?在此,討論將帶入時間點剛好落在《葉瑪》與《在棉花田的孤寂》演出後,於2018年12月8至9日舉辦的「EX-亞洲劇團演員訓練方法論壇」。該論壇以導演江譚佳彥(Chongtham Jayanta Meetei)近年在臺灣致力發展的「本質劇場」演員訓練方法為主軸,加上與談人相關觀察進行密集論壇,也包括其發展成果之階段性呈現。藉此,我們將視野轉入以臺灣在地身體為發展材料的演員訓練方法發展實例,作為比較與延伸。
二、多的可能:以EX-亞洲劇團「本質劇場」演員培訓計畫為例
論壇計畫由EX-亞洲劇團導演江譚佳彥、團長林浿安所主持;陳韻文引言;于善祿、羅仕龍、殷偉芳、蘇子中、林于竝、俄什姆.羅吉奧(Usham Rojio)擔任與談人;李昕宜、吳融霖、林緯、翁岱廉、陳寬田、葉柏芝、蔡秉軒、盧心怡、賴沛宜、譚志杰擔任呈現表演者。兩天早上為本質劇場不同階段的訓練方法呈現與討論;下午則由與談人各自發表其觀察主題。
在身體技術橫的移植觀點之中,被輸入方處於被動、無主體性的自我焦慮狀態。「被輸入」的想像結構,暗示了二元、單向的關係。然而從本質劇場訓練方法發起人江譚的身世上,輸入/輸出的二元性卻難以套用。他出生於印度,最早在1994到1997年師從Sanakhya Ebotombi,後來有段時間到德里國家戲劇學院,但江譚在當時對印度傳統表演方法沒有興趣。畢業以後他趕赴新加坡跨文化戲劇學校,踏入郭寶崑門下,學了六個月日本能劇、六個月印尼wayang wong傳統表演方法、兩個月京劇,這段時間他發現不同表演模式與印度傳統表演之間的關係,才又回過頭鑽研印度傳統表演。來臺灣以後,接觸到崑劇,也發現背後精神有許多跟印度傳統表演相近之處。基於自己所接觸戲劇領域之間的共通精神,便開始「本質劇場」演員訓練方法的發展計畫。他表示,本質劇場的訓練開始於臺灣,並可能只能發生於臺灣。如今已經在臺灣結婚生根的他,集合不同表演藝術脈絡,並以臺灣土生土長的身體為訓練對象,持續鑽研本質劇場體系的發展與內容。
因此,國族式的定義顯然並不適用於江譚。從地理空間與文化起源兩個層面來看,他的養分同時來自印度、新加坡、印尼、日本、中國、臺灣等。當主體複雜性遠大於國族概念所能籠罩的範圍,前者的豐富性、與後者的單薄便同時顯現。回頭來看,非常奇異地,當主體內在複雜性未能明顯超越國族定義範疇時,我們依然簡單地傾向以共同體思維當作辯證之重要軸線。這一點葉根泉早已於2014年明確指出【3】。但當每次外來文化強勢進入的現象重演,共同體式想像又會一再被深刻地召喚回來。東方的身體、中國的身體、臺灣的身體,這些詞彙為個人身體拋出一種質感一致的想像方式,使辯證與思考消耗於兩種截然不同的尺規間;其中,前者對於身體訓練發展的可能性無疑是有害的。它將「知識真理」已讓渡給「主體真理」的空間歸還,依其建構的框架進行填補與服膺。而葉根泉也在文中提供超越國族概念,以發展表演體系的反例:「日本暗黑舞踏開創者土方巽,心中所嚮往表現性的『東北』,就不是完全等同於自己日本東北秋田縣的家鄉,那不是一個家國概念下的地理位置,而是從如此風土的外在環境下,成長茁立出來一個特殊的自我,再從如此的主體性上頭,構造嶄新內在世界。」【4】個體對環境、風土的感受,這些奠基於地理空間內的元素,是身體變化與發展的材料;而其建立所的成果,則因為主體審美價值的消化、轉譯、與再表現,而超越了空間,成為由「主體真理」所主宰,「現實不存在的場所」(借日本評論者三上賀帶語)。
問題至此,再度被(良性地)拋回個體層次。我們可以比較明確地說,一個好的表演訓練系統,應該能穩定維繫主體內在與外在世界的溝通;而一個明確的表演風格,則奠基於明確的主體美感場域中。如此看來,江譚在介紹本質劇場之初,明確地區分表演的身體與生活的身體,對體系發展是有利的。除了在形而上的基礎面,避免了演員訓練因修身自我技術(techonologyj of the self)的性質,漸漸導向葛氏晚期全然著重內在探索而捨棄表演的可能性,也確保了體系能維繫內外在溝通的框架。
然而,儘管接受本質劇場演員培訓的學員背景殊異,範圍仍不離戲劇相關學院的學生演員、與對表演有意願投入的素人。因此在訓練之初,為了幫助學員進入狀況,江譚對外在形式的區分多有琢磨。他將身體質感與技術,區分為對眼神的訓練-集中、銳利(zoom in)/散焦、軟化(zoom out)、身體與呼吸節奏、台詞質感等;以及用心理狀態(mental)、聲音(vocal)、肢體(physical)作為表達工具的區分。在內在探索的面向上,江譚綜合自己的表演經驗,並廣閱心理學相關書籍,歸納出八種基本情緒,以編號(而非形容詞)命名,提供學員個別探索、自我認識的向度。
于善祿根據本質劇場細膩的身體質感區分,於論壇中指出體系的一種可能,是將表演記譜化,形成演員、導演討論時明確且客觀的平台,也在必要時作為穩定表演內容的工具。這是本質劇場演員訓練系統作為主體內在向外表達工具的優勢。另一方面,對主體內在的釐清與探索,目前透過八種基本情緒作為引導工具,也引起論壇聽眾和與談人產生諸多好奇:本質劇場該如何幫助其學員們持續擴展對內在的理解與感受,讓表演達到更細膩的表現層次?這或許是本質劇場在階段性地呈現後,接下來需面對與思考的問題。對於表演初學者而言,本質劇場以武術、舞蹈、瑜伽等形式為養分,搭配細膩的身體訓練,無疑提供相當清晰的架構與入門之道。然而這樣與大學學院表演訓練性質相近,引導入門的教育內容,是本質劇場的終極目標嗎?若想要將訓練內容往更進階的領域發展,培養出成熟、獨立、並能自我省思與提問的演員,那麼如何在維持個體殊異性的同時,協助其持續向內探索、並向外發展,以達到到更深層的表演狀態?過程中,哪些面向是本質劇場更偏重的?這些都留待更長時間的觀察與挖掘。
三、諸眾:主體的複雜性與反國族
地理空間與文化環境作為身體養成的成份之一,無疑值得去辨析。然而,在綜合《葉瑪》、《在棉花田的孤寂》、與江譚佳彥的本質劇場演員訓練系統的觀察後,可說明簡單快速地將身體論述與國族式共同體想像結合,無疑是將個體發展推入封閉的胡同。對此,蘇哲安在〈諸眾理論:初論未來政治主體的形象決斷與可塑性〉(2007)裡,試圖打破從帝國時期以降到當今國族主義,對政治主體單一想像的方式,並重新描述為,對所有個體重新辨認、歸納、與集合的成果。這與身體訓練和演員自我探索的本質不謀而合。
從這個角度切入《葉瑪》引發的討論,問題應該被重新理解為:演員們是否能夠、以及如何從新的表演訓練中,理解個別產生的內外在變化?因為在統一的表演風格裡,演出如劉純良所說,確實可見不同演員反覆消化吸收後的殊異性。然而此殊異可能來自任何原因,包括吸收程度、理解方式、背景養成等。演員是否因此拓展了其主體內外的溝通渠道與可能性?也難以在短時間內回答。現階段已經能更清楚辨析的是:《葉瑪》引起的不適,來自對文化不對等交流情境的直接聯想。去脈絡或表層的製作考量,可能使交流表象掩護國際代工的本質。但某特定文化脈絡的消失,並不等同該文化便會上升至共同體狀態,與其他文化產生對立關係。
一如沒有任何表演體系能代表臺灣,葛羅托斯基、麥可.契訶夫、特爾佐布勒斯也並不全然代言「西方」或任何國族。羅仕龍亦於EX-亞洲劇團所舉辦之論壇提到,我們所見相異文化地區的表演樣貌,都已經是該地理空間中,最國際化、與受鼓勵向外發表的選項了。國族定義在未來趨勢裡,應是討論文化與藝術時被適度捨棄的。此外,江譚的身世及其訓練體系,也微小、但明確地提醒了,主體的複雜性確實具有無限可能。辨認個體,以及演員修身的自我技術仍應被重新擺上第一順位。相形之下,國族與共同體式想像僅能以有限、且永遠遲到之姿,對有主體焦慮的人提供遙遠的慰藉,與溫暖的鄉愁。
註釋
1、葉根泉(2106),〈身體的實踐:八〇至九〇年代台灣現代劇場關照自我技術(1985-1996)〉。《身體技術作為功夫實踐:六〇至九〇年代台灣現代劇場的修「身」》(98頁),新北市:華藝學術,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2、劉純良,〈多重翻譯,由抽象至表演《葉瑪》〉。原文網址:https://pareviews.ncafroc.org.tw/?p=32513。
3、同註1,121頁。
4、同上註。
2019-02-18
原文網址連結:https://pareviews.ncafroc.org.tw/?p=33423